我们这一代生命中遭逢如此多的不可思议,无人记录恐怕是比默认更深的耻辱。———来自网络。
知青不仅是一千七百多万人共同的名称,更是我家诸多成员携带终身的印记。
2024年5月25至28日,第二届“中国知青作家杯”获奖文集《知青之歌》首发式暨颁奖典礼在中国现代文学馆隆重举行。承蒙组委会厚爱,我的长诗《寻找》,获得了诗歌类作品一等奖。
站在中国现代文学的最高殿堂,捧着大会颁发的获奖证书,我思绪绵绵,感慨万千,不禁自问:上山下乡运动已过去了半个多世纪,我们为什么还要写知青?
一九七九年,这场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……很有必要”的战役,终于打完了。绝大多数知青走过了漫长的严冬,迎来了莺*长的春天。
进入新世纪,老知青们陆续退出了工作岗位。在夕阳西下,倦鸟归林后,一些人拿起了笔,开始追忆似水年华,回首往日时光。我也打开了电脑,想留下自己的记录与思考。
这个巨大又残忍的数字,真实地呈现出在蔑视尊严、罔顾生命的大环境下,知青们付出的牺牲,我再次被惊到昏天黑地。因为我无论如何也想不到,在和平年代,竟会有那么多人倒在追求理想乌托邦的路上。
半个多世纪过去了,还有谁会记得那些矗立在荒野山林中的墓碑?还有谁会为墓碑下的人哭泣?只有他们的父母和挚爱亲朋。
想到他们的父母,我的心更像被撕裂成几瓣。知青都已垂垂老矣,长辈们绝大多数已经远行。即使健在,也都是耄耋老人。终其一生,他们都没能等到自己下乡的孩子,到死都不会合上双眼!
那一刻,什么小学生水平、写作技巧都被抛到了脑后。我打开电脑,写下了这首《寻找》。
对于批评,我虚心接受,并对诗歌进行了修改。此次获奖的就是修改后的作品。
面对质疑,我想说,任何个人都不可能掌握全国知青伤亡的宏观数据。但当年从国务院到各省地县,都有知青办公室。我就曾在某县知青办工作过,并负责管理知青档案。所以,这些数字应该来自知青管理部门。
作为上山下乡运动的亲历者,我们再提笔写知青时,更应该摈弃蒙昧与羁绊,直面曾经走过的弯路,客观公正地对这场运动进行深刻反思。
也有人读了诗歌,貌似公允地劝我,都这把年纪了,没必要再去纠缠历史旧账,要学会宽恕和遗忘。
至于宽恕和遗忘,我只想问一句,若死去的是你的兄弟姐妹,你是否还会说得如此轻飘,仿佛挥一挥手,就宽恕了那些罪恶,遗忘了那些牺牲。若如此,那良心真是被狗吃了。
出现这些声音我一点都不奇怪。因为对上山下乡运动的评价,在知青中一直都存在巨大的分歧,而造成这种分歧有多种原因。
以上种种,造成了每个知青对上山下乡的感受大相径庭,认知更是千差万别。我就曾听到城市底层的孩子说,到兵团或农场虽然劳动艰苦,但能挣工资补贴家用,自己也能填饱肚子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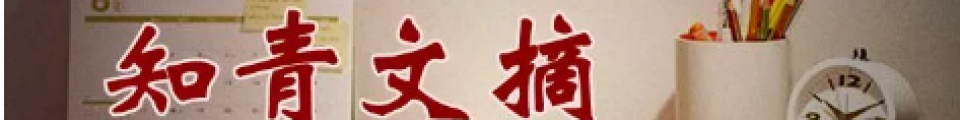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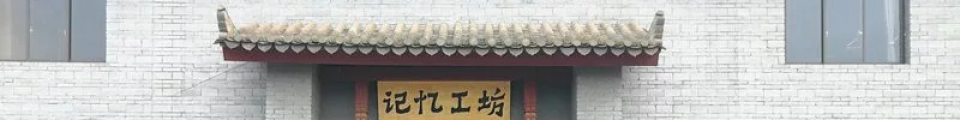



 查看资料
查看资料




 收藏
收藏 顶
顶  踩
踩 





